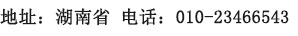本文转自:北京晚报
董梦知
我和纪宇都在青岛长大,可谓同乡;年轻时,我俩因写诗结识、结缘,可谓同好;退休前,我俩都在文联系统工作,他任青岛市文联主席,我在北京文联就职,可谓同行。我调到北京工作后,每次回青岛探亲,都会和他相聚;他来北京时只要有空,也会来家看我。一次,我带纪宇见了和我住在同一栋楼的《北京日报》的美术编辑王复羊老师,两位名家神交已久,见面后多有叙谈,王老师还给纪宇画了一幅肖像,用在他新出版的诗集上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,纪宇先以学生、后以工人的身份登上诗坛,受到社会 挚友的艺术成就让我激动不已。年春节我回青岛探亲,与纪宇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祝贺他的《风流歌》大获成功。他带我去了青岛人民广播电台,请编辑将春节诗歌晚会上朗诵《风流歌》的录音播给我听,还赠给我《风流歌》诗集。多少人为得到这本诗集费尽周折,而我唾手而得,真幸运!
为什么纪宇要写《风流歌》?众所周知,“风流”一词一直有褒义和贬义之分。那时,我国刚刚打开国门,禁锢多年的思想突然松了绑,很多年轻人思想紊乱,找不着北,纪宇就想用诗来诠释“风流”的真谛。但酝酿了好长时间,始终没有找到突破口。年3月,他在北京参加了诗人李季的追悼会,当他看到李季身穿石油工人的帆布工装、头戴铝盔,安静地躺着,想到李季在创作上曾给予他的热心指导,内心深受震撼。李季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投入到石油战线,写了大量讴歌石油工人的诗歌,被誉为“石油诗人”;他热爱石油工人,愿以石油工人的身份来定义自己的一生……这动人的场景犹如闪电,照亮了纪宇的思绪:风流!这才是真正的风流!他将原先积累的素材一泻而出,成就了《风流歌》。随着四川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诗集、各地报刊纷纷连载,《风流歌》成了抢手货,一时间洛阳纸贵。
其后五六年间,纪宇又写出《风流歌》之二和之三,其火热势头有增无减。读者的来信像雪片一样塞满了纪宇的信箱,至年,他收到的来信有上万封。这么多信,他无法一一回复,但有的信又不能不回,不妨举几个例子:老山前线的一位副指导员来信说,“战士听到电台播出的《风流歌》后,写信给电台索要原文,电台打印了寄来,战士们还不满足,总想得到整本诗集,希望朗诵着昂扬的诗篇去战斗”……后来,纪宇向老山前钱捐赠了五百本诗集。福建的一位女护士每年春节都给纪宇寄一箱水仙,她说纪宇的诗给了她光明和温暖,她要为纪宇的案头添一抹春色。还有一封信“写”在两张纸板上,是用针扎的密密麻麻的小豆豆——盲文!纸板中夹着一张译稿:“纪宇叔叔,你好,我是上海市盲童学校的学生。自从你的《风流歌》播出后,我就对你的诗歌充满了感情。我觉得你写出了八十年代青年的风貌,富有哲理性,我很喜欢。我虽然眼睛看不到,享受不到大自然的美景,但我可以张开理想的翅膀,到艺术的海洋里去遨游。我从小喜爱朗诵,去年参加了上海潮诗歌朗诵会的演出,得到了许多老演员的赞扬。他们还鼓励我自己创作诗歌,我开始创作了,但很不成熟……我在电台中听到许多朋友写信给你,向你要诗集,今天我这个盲女孩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信给你,希望能得到一些你写的诗和《风流歌》,如果你没有的话,请告诉我哪里有,我一定去买。最后我有个小小的建议,希望你能为我们盲孩子写一些诗,那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把它朗诵好。”纪宇不但满足了她的要求,还给她回了一封充满鼓励和关怀的长信。从她身上,纪宇“感受到作品能打动读者的那种幸福感和作家肩上的担当”。
听到这些故事,我的眼圈红了。《风流歌》之所以能打动亿万听众,是因为它说出了时代的心声、说出了人民的心声,这样的作品必是有生命力的——年,纪宇应邀对《风流歌》进行微调,增添了新时代的“风流新篇”。
这些年,在青岛老辈人中流传着一句谚语:“青岛的蛤蜊,纪宇的诗。”青岛人爱吃海鲜,蛤蜊是一年四季餐桌上的美味;将纪宇的诗与蛤蜊相提并论,可见纪宇在青岛人心中的分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