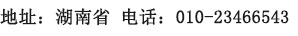本文由作者秋深诗意独家原创,转载请注明出处
《缚鸡行》
小奴缚鸡向市卖,鸡被缚急相喧争。家中厌鸡食虫蚁,不知鸡卖还遭烹。虫鸡于人何厚薄,吾叱奴人解其缚。鸡虫得失无了时,注目寒江倚山阔。
《缚鸡行》是大历元年()冬天杜甫寓居菱州西阁时所作。杜甫这一时期诗作的重要内容之一,是对一些社会人生问题作深沉的思考。如被认为“婆心太切”(王嗣奭语)的《又呈吴郎》,谆谆叮嘱借居镶西草堂的吴郎,对一个无食无儿的妇人要多一点怜悯之心,任她在堂前扑枣,不要干涉。
这种蔼然仁者之心还辐射到自然界里来,他不但“枣熟从人打”,而且“盘飨老夫食,分减及溪鱼”(《秋野五首》之一,从自己口里省下食物来喂给溪里的鱼吃。在收获的喜悦中,他更没有忘记仁民爱物,他说:“筑场怜穴蚁,拾穗许村童”(《暂往白帝复还东屯》)这种感情发自于对天下受欺凌、受损害的弱小者的同情。
咏物诗《麂》,就说得很透彻:“乱世轻全物,微声及祸枢。”可见诗人对自然的“物”的同情,还着眼于人类社会的乱世之悲。乱离之世,无论是人还是物都受到更加残酷的戕害,诗人深深憎恨这“衣冠兼盗贼,饕餮用斯须”(《麂》)的现实,追求“应宜各长幼,自此均勒敌”(《催宗文树鸡栅》)的各领长幼,均敌不争的理想。
为此,他曾催促儿子宗文修好鸡栅,“我宽缕蚁遭,彼免狐貉厄”(同上),使得虫不遭鸡食,鸡不被狐食。《缚鸡行》一诗,正集中表现了诗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。全诗从议论出发,首联点题,交待缘起。当“鸡被缚急相喧争”的时候,诗人的同情心油然而生。
德国的剧作家席勒说:“一切同情心都以受苦的想象为前提。”鸡在缚急时的“喧争”本不过是求生的本能,但是,又很容易引起诗人对于战乱中“被驱不异犬与鸡”的役夫之类的相似想象。问及缚鸡的原由,是家里的人嫌厌鸡食虫蚁。以下笔笔转,突出了鸡虫问题的矛盾:虫蚁固然可悯,但卖了鸡,鸡也逃不脱遭烹的命运。
《庄子·列御寇》早就阐述过这同样的问题:“在上为乌莺食,在下为缕蚁食,夺彼与此,何其偏也!”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引张远的话说,“虫鸡于人何厚薄”句“大有‘缕蚁何亲,鱼鼈何仇’意。”虫鸡于人既无所谓厚薄,不该厚虫而薄鸡,于是又命令奴人释鸡之缚。但是,释鸡而虫失,虫得而鸡失,诗人志在全物,却遇到了不可解决的难题。一时计无所出,只有斜倚山阁,注目寒江,沉入了深深的思索。
《论语·阳货》说,“予欲无言”;《庄子·齐物论》说,“大辩不言”。诗人从鸡虫得失这一件小事中联系到人世的纷争,这个道理无法用语言表达,也无须用语言表达,正所谓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”(陶渊明《饮酒》二十首之五),于是用描状作结。“注目寒江倚山阁”,是深思的情态。倚山阁,是居高;注目寒江,思潮亦如江水,滚滚滔滔,无休无尽;而天高水阔,又暗寓众生得失无了时这个命题的深广高妙,难于领悟,难于尽言。
关于这首诗的结尾,历代的诗评家多有好评。宋代的洪迈说:“此诗自是一段好议论,至结句之妙,非他人所能跋及也。”(《容斋三笔》卷五)宋人陈后山说:“谓鸡虫得失,不如两忘而寓于道。结句寄托深远。”(《杜诗镜铨》引)清代的沈德潜说:“宕开作结,妙不说尽。”(《唐诗别裁》)这个结尾的妙处,确实在于“含不尽之意,见于言外”。
洪迈曾举他的朋友李德远一首立意相同的诗《东西船行》为例:“东船得风帆席高,千里瞬息轻鸿毛。西船见笑苦迟钝,汗流撑折百张篱。明日风翻波浪异,西笑东船却如此。东西相笑无已时,我但行藏任天理。”这个结尾就比较直露。所以洪迈说:“只恐‘行藏任理’与‘注目寒江’之句,似不可同日而语。”(《容斋三笔》卷五)杜甫结句的妙处就在于:用情状描写暗示他在“想”,但并没说出他在想些什么。
人们见仁见智,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。谢师厚联系到治世的道理,说:“天下利害,当权轻重。除寇则劳民,爱民则养寇。与其养寇,孰若劳民;与其惜虫,孰若存鸡:此论圣人不易,天下亦无难处之事,始知浮屠法不可治世。”(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卷十八引)而浦起龙则认为“结语更超旷。盖物自不齐,功无兼济,但所存无间,便大造同流,其得其失,本来无了”(《读杜心解》卷二之三)。
从杜甫晚年溺佛,主慈悲不杀的事实来看,浦起龙的看法很有道理;而“劳民”与“除寇”的矛盾,在杜甫的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中,也有深刻的反映。可以说,杜甫这时从老庄的“齐物”到孔孟的“兼济”,其联想是十分复杂而深远的。只有宕开作结,才能启人思索,寓意无穷。
这种宕开一笔结尾的方法,经常被后代诗人运用来表现不言之大辩。如黄庭坚的“坐对真成被花恼,出门一笑大江横”(《水仙花》)、苏轼的“二虫愚智俱莫测,江边一笑无人识”(《二虫诗》)等都是,可见其影响之深广。
参考资料:古诗词
图片来源于网络,本文系作者秋深诗意独家原创,未经允许禁止转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