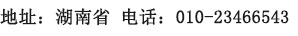“中原红木杯”
曾经一度薄情地以为,嗲嗲(dia,平声,指爷爷)与姆妈早已淡出了我的生活,只靠血缘关系维系着他们在我生命中的存在。
1.
二伯坐在廊前打盹。嗲嗲的气息,从他的脸部欢跃、升腾,在空气中弥漫,房子和院子的角角落落,嗲嗲的身影一会儿明朗清晰,一会儿隐隐约约。孩子们的打闹声,渲染着某种情绪席卷而来,躲避不及。低绾发髻的姆妈,俯身帮打瞌睡的嗲嗲掖好身上的小毯子,娇嗔,一百岁都跟细伢子样。起身间,她身上那一抹葱布兰像柳树头上晴空的蓝天,明媚、悠远。
毫无防备,就这样被旧时光偷袭。缱绻萦怀。
每次回家,我都要去老村转转,到伯伯家坐坐。细惹(二伯的老婆)是嗲嗲姆妈的养女,我出生之前,她便做了二伯的老婆,我们都叫她细惹。当年,姆妈把细惹当亲生的养,母女情深,细惹是重情分的人,她的双重身份,让她在我们心中有点特别。我虽然嘴里喊细惹,但心思跳跃,时常会当是姑姑。二伯和细惹住在小儿子家,屋基原是我们的老房子地基,当年的五树瓦屋,如今变成了并排两栋四层楼的别墅(伯父三儿和四儿一人一栋)。
高大的金色雕花镂空铁门内,比篮球场还要宽大的院子,前半部分被中间的水泥道一分为二,东北边以花树为主,这儿是二伯的主战场。二伯爱花草,认识很多草药,常常埋在我父亲买的书里,忘记晨昏,忘了田里等他使唤耕作的牛;东南边以蔬菜为主,菜园是细惹的阵地,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源源不断。后半部分是水泥空地,方便停车和行人。宽大的院子和两栋并排的四层楼房,有一种乡人的阔气。这儿是堂弟兵和双的家。孩子们在院子里玩沙,打闹。麻雀在矮挫挫的琵琶树、桃树、柚子树间飞来飞去,叽叽喳喳。院子外有块地势较低的空地,这块空地,我们叫门口墩。门口墩位于村庄正前方,是村中重要的公共场地。特别是做白喜事时,相沿成习的法事场地。门口墩北面有一口老井,双弟把挨着院子的老井也圈了起来,盖上顶棚方便了村里老人们在这浆洗。
老屋地基是祖宗留下来的,有嗲嗲姆妈的身影,有祖辈们的故事。
这儿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模样。记忆在这番新式的改造中显得尤为飘忽。不知缺席柳树和苦楝树的院子,嗲嗲姆妈能否习惯?
伯父和细惹在,堂兄弟和他们的孩子都在。我心释然。人在,亲情将会不断地延续。
2.
土地改革以后,嗲嗲姆妈为了送几个兔崽子们读书,家里成为长期的短工户。天意弄人,嗲嗲还不幸患上了哮喘。农忙的时候,大家都忙得脚不沾灰,他只能在晒场上“胡亥,胡亥”看场子。在村里备受冷眼。
嗲嗲没有嫡亲兄弟,只有一个出嫁了的妹妹,他与姆妈相依为命。困难时,孤独无援的感觉非常强烈。一个孤独的人,特别向往那种温暖而有力的关爱与帮助。嗲嗲那样痛苦、那样无助,姆妈无奈之下,痛下心把在南昌钢铁厂工作的大伯叫回了家。从此,大伯的理想破灭,他的命运永远与农村栓在一起。同时也在姆妈的心头落下了一块心病。大伯像圣斗士一样,带着无限的能量和温暖及时回到家中,把家庭拖出困境,父亲和叔叔也能正常上学。彼时,大伯代替嗲嗲做了半个家长。因此,父亲一直把大伯认定是他心中的爹。
年,父亲毕业于上饶卫校,姆妈担心老三的性命安危,强行把他叫了回来。忍饥挨饿都要出去读书的父亲,极不甘心地回到了家乡。邻居大妈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往事,说嗲嗲让父亲捡院子里牛粪时,父亲一脚把粪箕踢去老远,嘴里嘟囔,捡牛粪,捡牛粪,还不如死在外头。姆妈看着不说话,默默地转过身抹眼泪。由于嗲嗲的身体不好,姆妈既担当母亲的责任与义务,又扮演父亲的角色。
千辛万苦送孩子们出去,盼着能有出息,又因这样那样的事情,把放飞了的人儿拉回来。回的人不情不愿,拉的人手掌带血。
跟父亲同时的顺来在南昌工作,他的每次来信,都是他的家人炫耀的资本;屋后头的亮来在乐平机械厂工作,全家人都倍感荣幸;才祖在福建当兵复员回来在大队开拖拉机......姆妈每看到这些,也曾稍稍动心,想放父亲出去,给他自由的空间。这种心思才稍稍动了一下,姆妈又敏锐地发现,三儿子替人家看病看得好,给乡亲们带了便利,大家非常需要他。姆妈趁机宽慰父亲,毛叻,家里人都话俺生了个好儿子,生病息痛见不得侬,我跟侬爹听得真快活!侬一来做了好事,二来给我们长了脸!长了脸,姆妈说这三个字的时候,语气明显愉悦起来,中间那语音似乎还拐了个弯。
在家乡行医,与乡亲们打交道的过程中,父亲强烈感知到了他是一个被需要的人,也能体谅姆妈的话。远大理想是什么?夜深人静时,父亲常思考这个问题。能为大家排忧解难不也是生而为人的最大意义吗?父亲的“远大理想”悄悄内化成助人为乐的力量。
后来,面对土地又一次改革时,姆妈怕父亲在外村分田地,不回来,做了外村人,心生不舍。但又考虑我们村常遭水患,生活清苦,而父亲工作的地方,有饭吃,有柴烧,过日子不用愁。姆妈的内心十分纠结。
既然回到了家乡,父亲考虑再三,最终决定回家落户,守在父母身边,特别是他生病的老子需要他。
分田到户时,大队派了拖拉机去接,嗲嗲买了大鞭炮迎接我们回家。姆妈喜极而泣,抱着小弟弟一个劲地说,回来了就好,回来了就好。是姆妈的眼泪把父亲招回家的。我常这样想。
确切地说,我对于大家庭的认识也是从那时开始的。
我们回到家里,总共十八口人共住一栋房子,父亲与二伯分别做了廒间容身。大家庭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,家里要有多热闹就有多热闹。
姆妈颠着小脚,清瘦的身子忙进忙出,做饭、洗衣服、摘菜、养鸡、伺候猪牛等,像陀螺一样,一天到晚不得闲。不说别的,姆妈光是服伺妯娌四个的月子都够受的了。妯娌四个大生小生总共不下二十个月子,赶上寒冬,破冰徒手洗月子,那个冻,可想而知。她还不动声色地